|
 “石川河”的阎良、临潼段,“清河”的三原、阎良、临潼段以及“泔河”的礼泉到泾河段都是我们伟大先祖所开凿的“水渠”、是我们伟大先祖最早的水利工程的遗留。 “石川河”的阎良、临潼段,“清河”的三原、阎良、临潼段以及“泔河”的礼泉到泾河段都是我们伟大先祖所开凿的“水渠”、是我们伟大先祖最早的水利工程的遗留。
石川河古称“沮水”,也称“漆水”,“漆水”只是石川河上游的一条之流,因此,石川河就是“沮水”。古书早有记载,石川河为沮水,东流入“泽”(雷泽),然后与洛水汇合后入渭(河)。《诗经·绵》有“绵绵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漆沮。”之句。《汉书?地理志》:“直路(今富县西南),沮水出,东入洛”,清末陕西大儒牛兆濂为祖父任明都撰写的墓志铭,内有诗一首,其中有: “漆沮之侧,荆山之阳,殡隐君子,后福无疆。”之句。《雍录》见其卷六第121页所载:禹贡漆沮石川河之 条下写道:“《禹贡》漆沮,惟石川河正当其地,它皆也。”第123页又写道:“《禹贡》之谓漆沮者,即富平县石川河,至白水县入洛,而与洛水俱自朝邑入渭者也……。”
但是,后世又对与“沮水”争论不休,源于沮水的流向有了变化,以至于有人直接将郑国渠、白渠认为是“沮水”。其实,“沮水”就是石川河,石川河就是“沮水”。之所以后人产生了众多误会,是因为石川河在古代的确进行了九十度的改道,并且这次改道还是人为的,这个人就是大禹。
所谓的大禹治水就是将石川河改道,将石川河在荆山塬处由以前的东流入洛,改为南流入渭。具体就是先在荆山塬断塬处到渭河之间修上一条渠,然后再将断塬处打开一条豁口,引石川河水南流而下。大禹之所以要治水,我在《大禹治水在阎良》一文中已有论述,一是因为石川河东流入要经过今天的卤阳湖(古称雷泽)然后才与洛河汇流进入黄河或渭河(因为古代这一块总是泛滥,黄渭不分)。而卤阳湖地区范围宽广,当石川河一发大水,就会洪水四溢,淹没大禹部落的村庄和耕地;二是要开凿一条渠来灌溉今天阎良和临潼的一大片土地。
当然,要一条水渠逐渐成为一条河流是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还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水源要不断有保障,二是水渠的河床要不断地下陷。而这两个因素石川河全都具备,一是古人不断地去荆山塬的土来填堵石川河东去的河道,另一方面是从石川河入渭处从一开始就不断地塌陷,以逐步后退向北的状态在地面形成一个深沟。
在这个漫长的过程里,才有了“沮水”东流入洛和南流入渭两种常态,使得古人究竟搞不清阎良和临潼这段石川河究竟是“河”还是“渠”。
过了大约两千到一千年以后,在这片大地上又出现了一个崇拜“大禹”的水利工程师,他就是韩人郑国。郑国将泾河之水通过一条人工渠注入到了秦国故都栎阳的南边石川河,也就是今天的相桥镇。郑国本来就没打算将渠修到泾河,而是修到今天的三原县城,将较小的清河进行截留,抬高水位入渠。本来这就算完工了,可是秦国又不允许,嫌水量太小,让他继续向西修,要将泾河之水也引过来。郑国也明白引泾河水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截留泾河在古代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可秦国政府威胁郑国,如果不修的话就是就杀了他,并且说他是来“疲秦”而不是“助秦”。郑国无法,只好在继续修到泾河,筑坝引水。
可是,官僚主义害死人。郑国死后,泾河大坝也没有保留多长时间就被水冲垮了,但是估计秦国为了面子不不断地让人在继续筑坝。最后,秦国灭亡后,几经战乱,到了汉朝建立的很长一段时期,郑国渠真正发挥作用的也就是现在的三原到相桥段。汉朝吸取了秦国教训,总结经验,认为在泾河筑坝那是不科学的,但是光靠清河的水也是不够的,再说了也想超越秦国灌溉更大的土地面积。因此,伟大的汉武帝下面又有一个水利专家叫白公,他有一个新的建议,可以一举两得,既能给郑国渠注入更大的水量,又能灌溉更多的农田。那就是从郑国当年的泾河引水处再继续向西修渠,一直修到现在的礼泉县,将那里的一条和清河流量相当的泔河进行截留,既能灌溉礼泉到泾河之间的农田,并且在用这条水的下泄之势经过泾河注入到郑国渠里。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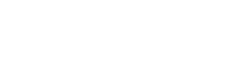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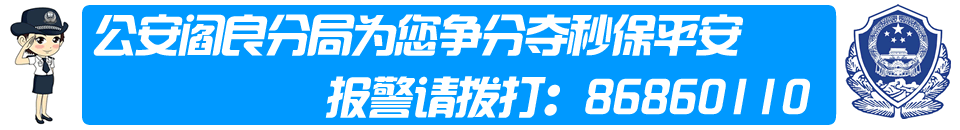



 发表于 2010-10-18 23:01:00
发表于 2010-10-18 23:0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