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古代典籍中,不止一次地提到了大禹:
1、“信彼南山,维禹甸之。”(《诗经?小雅?信南山》)
2、“丰水东注,维禹之绩。”(《诗经?大雅?文王有声》)
3、“奕奕梁山,维禹甸之。”(《诗经?大雅?韩奕》)
4、“奄下有土,缵禹之绪。”(《诗·鲁颂·闷宫》)
5、“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诗经?商颂?长发》)
6、“设都于禹之绩。”(《诗经?商颂?殷武》)
7、“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尚书?洪范》)
8、“以陟禹之迹。”(《尚书?立政》)
9、“禹平水土,主名山川。”(《尚书?吕刑》)
在青铜器鼎文里也有大禹的记载:
1. 《齐侯钟》有言:“……成唐(汤),有严在帝所,敷受天命……咸有九州,处禹之堵。”(《齐侯钟》是齐灵公(前581-553)之器)
2. 《秦公簋》也谈到了“禹赍(迹)”(《秦公簋》是秦景公(前576-536)之器)
3. 2005年,保利艺术博物馆的专家在香港古董市场上,偶然发现了一件西周中期的青铜器《遂公簋》。遂是西周的一个封国,在今山东宁阳西北与肥城接界处。此器造于距离现在大约2900年前,有98字的长篇铭文。铭文的中心内容是讲“德政”。开篇言“天命禹傅士,隋(堕)山浚川”,将大禹治水的文献记载提前了六七百年。它的被发现,震惊了史学界。
我们着重讨论下面几个古今争议最大的关键词:丰水东注
何谓“丰水东注”?在古今对大禹的事迹的讨论中,经常回避这个词,甚至还有的人将今天西安西南方的那条“沣河”来牵强附会,如果那样的话,古人直接就说“沣”而不是“丰”了。
其实,“丰”应该是通“封”,“丰水东注”意思就是说,将水截留,不让它再向东流去。当然,这样孤立的解释也根本没有意义,而要将下面的信息综合起来。
“甸之”、“奄下有土”、“ 敷下土方”、“ 平水土”、“ 主名山川”、“堵”、“ 隋(堕)山浚川”
其实,说的已经再明白不过了,大禹治水几个细节是不可抹杀的:挖土、运土、将土投入到水中、垫高、封堵河流、开凿山川(塬,古人将土堆夸大为山)、导流排水。
可是到了汉朝,那些人为了体现“天人合一”、“君命天授”的理念,不断地将原有的故事给予神话和夸大扭曲,使得后人也跟着云里雾里。
大禹治水的真实面目是这样的:
在距今4000年前到3000年之间,在渭河北岸到梁山塬(今天大荔北部土塬,今讹传为“镰山”)之间,沿洛河两岸,有一部落群繁衍生息于此,当时还处于新石器父系社会,他们的生活生产方式基本介于农耕和游牧之间。当时这个地区,气候温和,水茂草丰,野兽出没,但也最适合原始部落的生存。在这片土地的西北,有一个大湖,古人称为“雷泽”,水面渺无边际。但是这个湖会经常不间断地进行泛滥,淹没这些部落的居住地和耕地,这些部落的首领开始想着如何治理这个水患。最开始他们的首领叫做鲧,带领他们治水,经过很长时间勘测,他们发现这个大湖的源头在今天的荆山塬北侧,由一条叫“沮水”的河流注入。因此,鲧带领部落的人,开始将荆山塬的土挖起来,用肩挑人抬的方式,不断地填沮水,组织它继续东流。过了很多年,虽然土填了很多,但是成绩不大。鲧死后,他的儿子继承了父亲的事业,在一方面继续挑土填河的同时,有带领部落在荆山塬的南侧开辟一条水渠直通渭河,然后再将荆山塬挖出一条豁口,在不断填土阻止沮水东流的同时,水位不断地抬高,终于从荆山塬断塬处,顺着渠道流向渭河。在大禹死后,他的后人不断地继续他的事业,沮水在荆山塬断塬处的豁口也不断地变大、变深,终于将沮水彻底改道,彻底地解决了他们原来族人的居住生活之地的水患。
在进行这项治水工程的时候,大多数人都是在荆山塬上或者两边工作,因此,生火做饭自然是在荆山塬上了。于是,在许多年里几乎整个荆山塬炊烟不断。春秋战国人士按照周朝的礼仪,将此讹传为黄帝曾在此铸鼎,为庆祝胜利和会盟诸侯。
后来,中国上古流传的“大禹治水”、“黄帝铸鼎”、“愚公移山”、“精卫填海”的神话故事,其实,这些都是说的同一件事,都是我们古代伟大先祖在与自然抗衡和斗争的真实写照。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10-19 15:30:44编辑过]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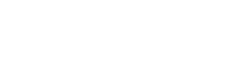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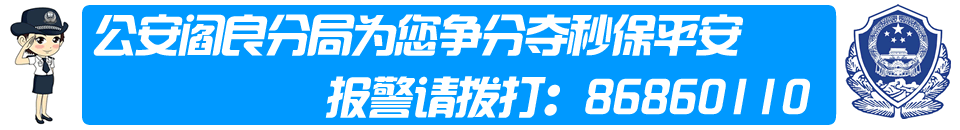



 发表于 2010-10-19 15:18:00
发表于 2010-10-19 15:18:00